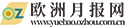这是20世纪最后一年的记忆。
记忆里每个周末,他总是坐上公交车从复旦大学所在的五角场出发,穿过热闹的街市、穿过车流穿梭的跨越苏州河面的桥、穿过人来人往的外滩,到达熙熙攘攘的董家渡,然后下车登摆渡。随着船身开动,江风拂面,高歌猛进的市区渐渐安静下来,远去了——按照大人的要求,这个“在大学食堂里怎么可能吃得好”的大一新生,必须要去黄浦江那一边的祖父母家“补补身体”。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总是在黄昏时分,他走进祖父母家所在的微山新村。眼前的景色与浦西迥异。小区的树荫下,有老年人在摇着扇子乘凉,有人在搓麻将,走进楼道时,能闻见有人在煎咸带鱼。
一切都是慢悠悠的,他觉得时间仿佛在这个小区里停滞了。这停滞让他感到焦躁,他觉得这不是年轻人应该来的地方,他觉得抵触。他渐渐缩短了在小区里停留的时间:从待满整个周末,到只待一天,到最后他匆匆吃完晚饭,不顾祖父母的挽留,又连夜赶回学校。他说,那个时候不想再去微山新村了,他要投入火热的城市节奏,要像一个真正的上海青年那么生活着。
至于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也许从一开始到现在,金理始终在琢磨。
5岁的金理在微山新村(金理 提供)
1
有一个疑惑,是关于微山新村出现的时间。
在房产中介的介绍中,微山新村“建于1988年”。然而,在金理的记忆里,大人们都笃定地告诉他,1981年他出生后,母亲把他从医院抱回了微山新村。1982年本市媒体一则《本市启用一批新地名》的短消息,则将微山新村名称的出现正式确定在了当年9月:
“经市府批准,从即日起启用五个新村、三十二条道路新地名;取消二条路名,更改一条路名。五个新村为:普陀区的桂巷新村;南市区的上南新村、微山新村、南码头新村;虹口区的曲阳新村。”
的确,在当时,微山新村虽然地属浦东地区,但行政上与旧上海县的政治中心老城厢同归南市区管辖。金理出生的那一年,正是浦东地区开始新建一些新村的时候。在旧闻报道中,还可窥见当时这里初建时的样貌:“1981年10月,浦东的一些新村建成后,道路高低不平、路灯不足,缺少公共厕所。副区长和城建、住宅办的干部察看后,当即派施工队伍进入现场。现在上钢一村和四村的一条两百米长的崎岖道路正在抓紧修复,昌乐路、徐家宅路等5条马路的修复计划也已落实。上南二村的26幢新工房没有路灯,他们就和浦东供电所商量,目前已装上了路灯。胶南、微山新村的路灯装修计划,也已落实。”
2000年,上海市政府宣布取消南市区,将南市区黄浦江西岸地区并入黄浦区。原南市区黄浦江东岸地区,在1993年浦东新区建区后不久并入浦东新区。
2
新生的小孩不会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建筑几乎与自己是同龄人,自己所处的区域也以自己的方式在“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相比当时浦西地区的城市化程度,浦东始终像是一个赤脚追赶的后进者。但前浪与后浪、成熟与新生的界定,究竟应该划分在什么地方呢?站在1999年,往浦东、浦西两边看,哪一边更时尚、更成熟,毋庸置疑。可是如果时光再往前推呢?
比如说,把时间推到明朝万历年间,上海浦东地区的南码头的前身南仓渡与董家渡、杨家渡等并称为黄浦江八大渡口,是当时浦东地区最大的私人粮仓渡口。近代,民族工业兴起,这里演变成化工厂、造船厂等集中的工业区域。金理的祖父母之所以会住在微山新村,原因就是他们任职的单位即上海溶剂厂。
这是一家被称为“远东第一”、堪称当时亚洲最大的酒精厂。地方志显示:位于南码头的上海溶剂厂,原为印尼华侨黄江泉、黄宗孝在1933年投资,1934年创办,称中国酒精厂。“用自南洋输入的甘蔗糖蜜为制造酒精的原料,日产酒精7000加仑,纯度达96%至97%。”1934年1月19日,黄宗孝为了纪念其父黄仲涵的爱国精神,在工厂办公楼制作并悬挂匾额,上书“继父前辉”四字,至今仍保留在上海溶剂厂近代建筑群内。
中国酒精厂是当时华侨资本在国内投资和建成投产的较大企业。参与中国酒精厂筹建的中方专家有工业微生物学家陈騊声(1899—1992),中国微生物学家、应用化学家、中国近代工业微生物的先驱魏喦寿(1900—1973),还有化学工程学家顾毓珍(1907—1968)等等,汇聚了当时国内化工行业的精英。(《世博村里的近代民族工业老厂》宋飞波)
当时,中国的酒精大部分靠外国输入,该厂填补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空白。然而,1937年日寇侵占上海后,工厂停工,厂地闲置。直至1954年,筹建上海溶剂厂,1956年初投产,生产总溶剂、丙酮、丁醇、乙醇,总溶剂产量2000吨,产值416万元。1980年生产28种产品,产量10万吨,产值14100万元,是上海市著名的化工厂之一。
当祖父母在这里上班时,这家厂是具有先驱性的,在这里从事的工作是有创新性的,能住进微山新村是最时髦的。
3
在新世纪初,生于微山新村、长在微山新村的金理,却看不上这里的陈旧和缓慢,觉得这里“不够上海”。
他是知青子女,童年一多半时间要随父母回无锡硕放念书。硕放距离无锡市中心直线距离10.8公里,距离苏州市中心直线距离28.7公里。每逢寒暑假到上海,金理总是委屈地发现,流行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大家讨论什么好看的电视剧和电影,他总是慢人一拍,在上海的堂兄弟姐妹早就知道了。这一拍的距离,看上去很容易赶上,却总是赶不上,这令人抓狂,令年轻的金理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上海人”。而生活在浦东的微山新村——唯恐他在大学食堂吃不饱的奶奶、慢慢腌制老家绍兴苋菜梗的爷爷、拿着鸡过来央求切成白斩鸡的邻居……熟人社会过于亲密的关系,还有一开窗从南码头边工厂吹过来的灰扑扑的风,是多么不精致,不够“梧桐区”、不够传奇、不够拿得出手。
那个时候,年轻的金理概念里的上海,是每周同学们去买的《申江服务导报》《上海一周》里建构的上海,是外出实习的女同学越来越精致的服饰妆容中揭示的上海,是他在无锡郊区生活时一遍遍想象过的上海。他以研究上海都市时尚报刊为题,和一位来自上海金山的同学一起写了研究论文。金理唯恐两人不够格,复旦大学的张新颖老师却鼓励他们用“有别于土著”的眼睛来审视这座城市的表达。
也是在新世纪初,“上海溶剂厂近代建筑群”由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公布为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单位。为了留住城市历史记忆,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时,保留了上海溶剂厂、上海港口机械厂留下的部分老建筑。经过保护修缮与合理利用,上海溶剂厂近代建筑群已成为承载浓厚历史积淀的世博村的组成部分。
新与旧,原来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当时光流逝、祖父母去世,当全家人逐渐搬离微山新村而散入各处新居时,金理这才有机会重新回忆1999年来到微山新村的傍晚。新村里的居民完全不像他以为的那么无所作为,而见证民族工业和浦东开发开放的新村本身也完全不像他偏见认定的那么“不够上海”。这里也是上海。不是那种时髦女郎和精致消费品构建的上海,却把上海幻化进更深层的日常里去了。
如今,从微山新村可以一直走到南码头江边。新修好的滨江步道上江风吹来,金理想起大学时嫌弃地逃离这里的日子。也许现在,他终于把握住了一点上海。
少年金理与父亲(金理 提供)
金理在微山新村旧居前留念(金理 提供)